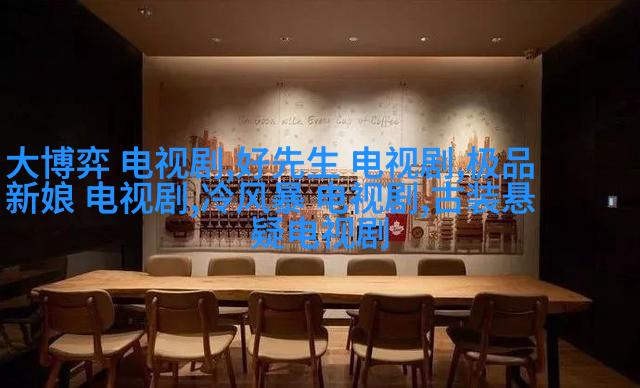网红雪梨的大学梦想
1981年,我们高考时,是分数公布后才填报志愿的。在云南,我的考分算是蛮高了,但限于家庭经济原因,父母要我选择去读无需伙食费的师范大学。那时我15岁未满,自然都听父母的,因此选择就只有两个,要么北京师大,要么华东师大。尽管在此之前,北京上海都只在图片和书籍中见过,但我竟然毫不犹豫选择了上海,第一、二、三志愿填的都是华师大,中文系、教育系和历史系。可能这就是缘分吧。被教育系录取后,我得知同级入校的那位中文系同学考分并不比我高,让我郁闷了很长一段时间。

中文系中的格非同学写过一篇题名为《师大忆旧》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刚一进校,我们即被高年级的同学告知:成为一个好学生的首要前提就是不上课……我们当时少不更事,不知学术为何物,只玩性未泯,便喜出望外,将其奉为金科玉律……好在老师们大都宅心仁厚,从不与学生为难,我们即便不去听课,却能考个七八十分并非难事。”诚哉斯言。当是我之时,只除了心理学和大学语文,这些课程,我十之不得意,就常常翘课,看那些开禁不久的世界文学名著,或蹭听中文系的小组讨论,或喝酒踢球,或到文史楼通宵亮灯103教室里写诗、写散文或小说。这可以肯定,在教育系师生眼里,我四年间,都不是一个好学生。但令我感激终身的是,因为对这些课程仅知一鳞半爪,在1985年的毕业典礼上,被母校误认为“云南师大的中文系”毕业生,以至于连云南省也以为华东师大的荒唐走板搞错了!
说起来,其实我的游荡是有由来的。我记得是在入学后的某个月亮很白的晚上,一群人聚集在明亮而简陋空房间里,为夏雨诗社招新成员举行赛诗会。你可以想象,当文学热潮如火如荼地席卷高校,那参与的人必定也是乌泱泱的一群。我紧皱眉头,在规定时间内作了一首叫《白墙》的短诗歌,它意外地获得了比赛第一名,并登上了次日校刊。我那刚刚进入十六岁的小心脏啊,对这个突如其来的荣誉感到非常激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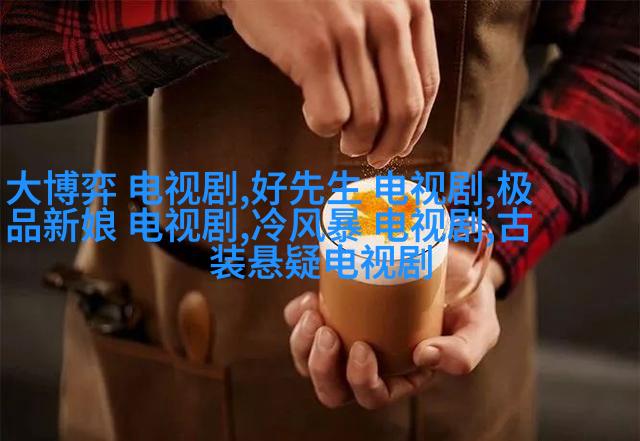
遗憾的是,《白墙》之后,我再也无法创作出像样的作品。不过没多久,又成立了华东师大的散文社,还出版了《散花》杂志。我送去了大量自认为是小说或散文但实际内容模糊的事物,而第一期《散花》就刊登了一篇关于童年的回忆文章,还被赵丽宏选入他们杂志发表——这是第一次变成铅字,让我兴奋又骄傲。一发而不可收拾,由此开始,每篇作品似乎都找到了合适的地方发表:《童年的秋天》、《学院六人图》,甚至连北村先生转载的情节也不乏其例。
文史楼103教室成了我们夜以继日工作的地方——因为宿舍关灯后,这个地方成了陈丹燕、戴舫、祝春亭等人的秘密基地。在九十年代末,当阮光页先生提出“华东师大作家群”这一概念时,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因为就在那个时代,有这样一批人,他们以文学作为生活的一部分,不断探索着自己的世界。

话说来,当王焰任职社长的时候,他和格非做主编,我们负责编辑出版杂志。而王焰和格非都是天天向上的好孩子,所以他们绝不会耽误学习,所以主编杂志,就成了我们的主要工作之一。不幸的是,那些最初塞进杂誌里的故事,如《城疫》、《烧炭老人》,后来竟然还有人把它们发表给别的地面媒体,这让我深感愧疚,因为原本这些应该是纯粹的心灵输出,而现在却变成了其他目的下的工具。所以三十多年之后,我必须对王焰和格非假装没看见宽宏大量,再次表示敬意。
当然,也有一些讲座,与李泽厚、李欧梵等前辈一样,他们的话语仿佛迷雾般轻轻飘落,却让人久久不能忘怀。而每一次他们踏足华东師大的演讲厅,无疑都会将文化与文学浓缩成一种独特气息,使得任何时候都不曾失去它所吸引人的魔力,即使是在八十年代火热的时候,也能吸引到各界宾客围观,如程永新、高阳等众多大家。但每一次结束,都像是风起云涌般消逝,不留下痕迹,只留给我个人作品讨论会上的温暖回忆,那场活动中陈村教授及其他许多已成名者亲临捧场,让今天看来仍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感纠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