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最大网红排名我的大学生涯火遍网络
1981年,我们高考时,分数公布后才填报志愿。在云南,我的成绩算是相当不错,但受限于家庭经济状况,我不得不选择读师范大学。那时候我15岁,还未满18岁,所以一切听父母的指示。因此,我只能选择两个学校:北京师大或华东师大。我在北京上海都只在图片和书籍中见过,但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上海。我填写的志愿全都是华师大的中文系、教育系和历史系。也许这就是缘分吧。当我被教育系录取后,得知同级入校的中文系同学成绩并不比我低,这让我感到非常失望。

记得刚进校时,我们即被高年级学生告知:“成为一个好学生的首要前提,就是不上课……我们当时少不更事,玩性未泯,不知道学术为何物,所以自然喜出望外,奉为金科玉律……好在老师们大都宅心仁厚,从不与学生为难,我们即便不去听课,考前突击两周,就能考到七八十分也不难。”诚哉斯言。当时除了心理学和大学语文课程之外,我对教育系设置的其他课程都不感兴趣,因此经常翘课,在图书馆看那些新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或蹭听中文系的课,或喝酒踢球,或去文史楼通宵亮灯的地方写诗、散文。这可以肯定,在四年的时间里,在教育系师生的眼里,我从来不是个好学生。但是,因为对这些课程了解很少,当1985年毕业的时候,因为分配证上的“云南师大中文系”,母校竟然给我填写成了“华东师大中文系”,连云南師大的人都以为华東師大學荒唐走板,把情况搞错了!
说起来,其实我的无所事事有其由来。在我们入学初期,有一天夜晚,一群包括李其刚、宋琳、徐芳、张小波等人的夏雨诗社招募新成员。在那间明亮而简陋的小房间里,他们举办了一次新同学作诗会。你可以想象,那时候文学热潮正盛,在高校中若是不加入文学社团,那简直太丢人了。所以在那个月光洒满白色的晚上,当15分钟内自拟题目作一首诗歌长短参差无定的场合下,我紧皱眉头,用规定时间内创作了一首叫《白墙》的短篇作品,没有记录具体内容,但当晚意外地赢得第一名,并登上了次日校刊。我那个刚进入16岁的小心脏啊,如同今天买体彩中五百万的大奖者一般激动。不久之后,即成为了夏雨诗社的一员,对自己似乎注定要投身于文学界深信坚定。

遗憾的是,《白墙》之后,再也无法持续创作出优美文字。不过没多久,又有查建渝、祝春亭等学长成立了华东師大散文社,还创办了刻印《散花》杂志。我送出了许多不知小说还是散文的手稿,其中之一发表在《散花》第一期,被赵丽宏选登至他们刊物——那是我第一次变成铅字,也是我有生以来最傲娇的事情。一发不可收拾,以后的文章陆续发表,《童年的秋天》发表于《儿童文学》,小说《学院六人图》被转载至《小说月报》,于是文史楼103教室成了我们的夜宿之所——因为在四年的时间里,一批批人的身影,都曾穿梭于这个通宵亮灯的地方。
随着时间流逝,当出版社阮光页先生九十年代末提出“华东師大人士群”这一概念时,我一点惊讶感也没有。话说王焰担任主编期间,与格非合作编辑杂志,是一次美好的经历,他俩都是天天向上的好孩子,从不会耽误学习,所以主编工作就落到了一个杂牌军手中的位置。虽然最初将一些私货塞进杂志,但如今回忆起那些作品,如《城疫》、《烧炭老人》,它们最初是在这里见世面,它们现在已经远扬海外,而评论与推荐,也已成为过去。而对于王焰和格非他们假装没看见宽宏大量的事实,我必须表示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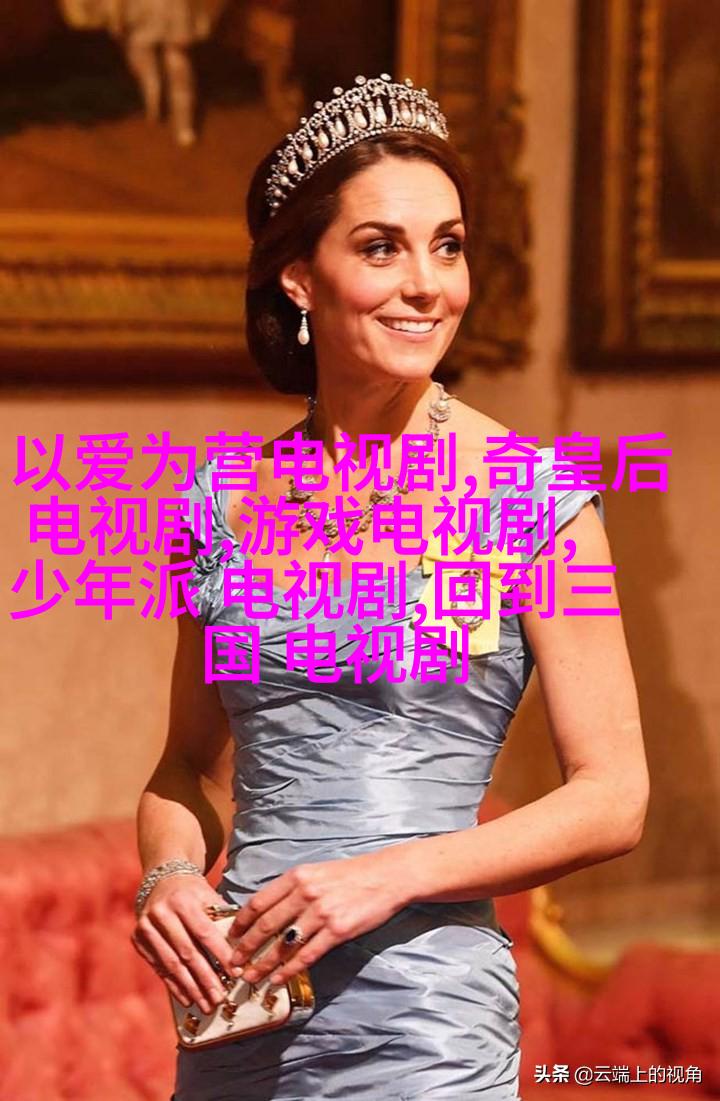
最后,由於三十多年后的今日,对此情此景仍怀念且感激,让我再次站出来,为王焰他们假装没看见宽宏大量的事实表示由衷敬意,以及对那段青澀歲月充滿無限懷念與感激的心情。这是一段关于梦想实现途中的点滴回忆,是关于青春时代追求真理与艺术的一段传奇故事,是关于友谊与爱情交织的人生旅程。这也是为什么,无论未来如何发展变化,只要有这样的记忆,就足以让我们坚守自己的追求,不忘初心,为梦想奋斗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