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生涯中国10大网红故事
我的大学生涯:中国10大网红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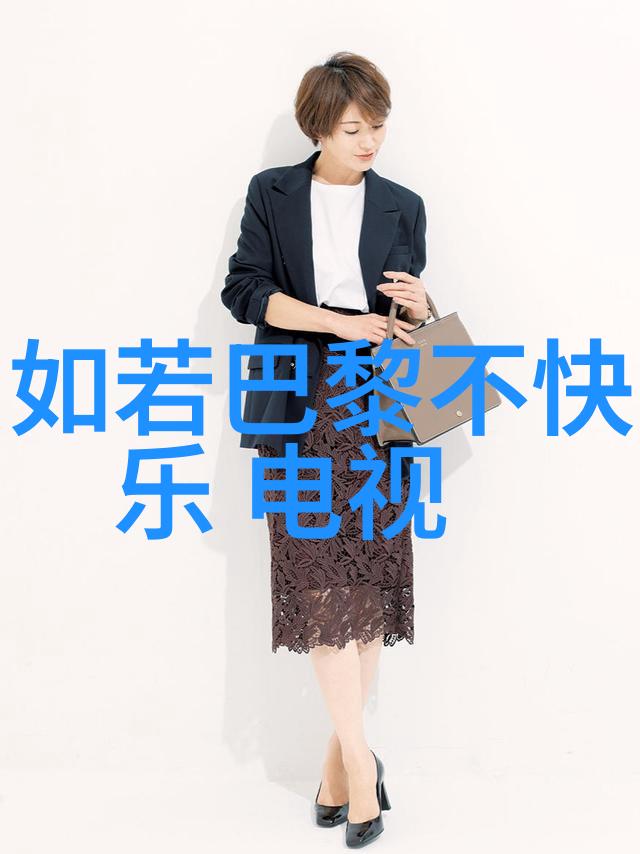
1981年,我们高考时,分数公布后才填报志愿。在云南,我15岁未满的考分算是蛮高了,但限于家庭经济原因,父母要我选择去读无需伙食费的师范大学。那时,我自然都听父母的,因此选择就只有两个,要么北京师大,要么华东师大。尽管在此之前,北京上海都只在图片和书籍中见过,但我竟然毫不犹豫选择了上海,第一、二、三志愿填的都是华师大,中文系、教育系和历史系。可能这就是缘分吧。被教育系录取后,得知同级入校的那位中文系同学考分并不比我高,让我郁闷了很长一段时间。
中文系的格非同学写过一篇题名为《师大忆旧》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刚一进校,我们即被高年级的同学告知:成为一个好学生的首要前提就是不上课……我们当时少不更事,玩性未泯,不知学术为何物,自然喜出望外,奉为金科玉律……好在老师们大都宅心仁厚,从不与学生为难,我们即便不去听课,考前突击两周,考个七八十分并非难事。”诚哉斯言。当是之时,只除了心理学和大学语文,就喜欢上了那些开禁不久的世界文学名著,也常常翘课到图书馆看,或蹭听中文系课,或喝酒踢球,或到文史楼通宵亮灯的地方写诗、散文。我可以肯定,在四年的时间里,在教育系师生眼里,我都不是一个好同学。但令我感激终身的是,因为对教育系课程仅知其一鳞半爪,当1985年毕业,被母校居然给填写成了“云南师大的中文系”,以至于连云南省也以为华东师大的荒唐走板搞错了!

说起来,其实我的不务正业是有由来的。记得是在入学未久的时候,一群热情似火的人,为夏雨诗社招募新成员。在那个月光明媚而又充满期待的大晚上,他们组织了一次新生的诗会。你可以想象,那时候文学热潮如火如荼,在高校里加入文学社团简直是一种必需。而那天夜晚,与李其刚、宋琳、徐芳、张小波等人一起参加赛诗的人,无疑也是乌泱泱的一片。我紧皱眉头,在规定时间内作了一首叫《白墙》的短诗歌,它意外地获得第一名,还登上了次日校刊,这让我感到无比兴奋。
然而,《白墙》之后,我竟然再也无法创作出像样的文字。但幸运的是,不久之后查建渝、祝春亭等学长们,又成立了华东师大的散文社,并创办了《散花》校园杂志。我送出了许多小说或散文作品,而第一期《散花》就刊登了那篇《赤足童年》,还被赵丽宏选发表——这是我第一次变成铅字。这发端使我的作品纷纷见诸各类出版社,如《童年的秋天》、《学院六人图》,甚至还有些转载在其他重要媒体...

文史楼103教室,是我们夜不能归宿的地方——因为在四年的学习生活中,那里的身影,都曾经历迁移而来,有陈丹燕、戴舫等人的脚步声响起,有祝春亭和宋琳的声音回荡......所以当阮光页先生九十年代末提出“华东師大的作家群”这一概念时,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惊讶。
话说回来,当王焰任命为我们的主编,他是我这个杂牌军中的另一个合作伙伴。他以及格非都是天天向上的好孩子,所以他们从没耽误学习,而主编这本集子,就成了我的工作之一。不论是最初的小说如《城疫》,还是稍长一些的小说如《烧炭老人》,它们最初都是塞进这本集子的私货。但尽管如此,这些作品后来分别发表于北村编辑部下的福建文学及清明杂志,这一切源头,都得追溯到华东師大的散文社。我对王焰他们假装没看见宽宏大量的事迹深感敬意。

格非再次提及,“学校演讲报告会研讨会盛况恐怕与别处也没有什么不同”,但对此言我略存异议,即便李泽厚李欧梵这些前辈,以及近水楼台的大人们施蛰存许杰徐中玉钱谷融戴厚英裘小龙李劼等,他们虽然能请请来,但是每一次讲演,都布下文化雾霭,以至于当时声名显赫者,如王安忆陈村马原苏童程永新吴亮孙甘露北村等,每个人都会愿意留下来流连其中。这让我至今仍觉温暖。当2015年4月17日站在昆明西坝坊街口看着繁忙的人流,将这些往事抛掠脑海,再回望那些曾经拥有梦想与激情的心灵,你是否仍能感觉到那种淡淡的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