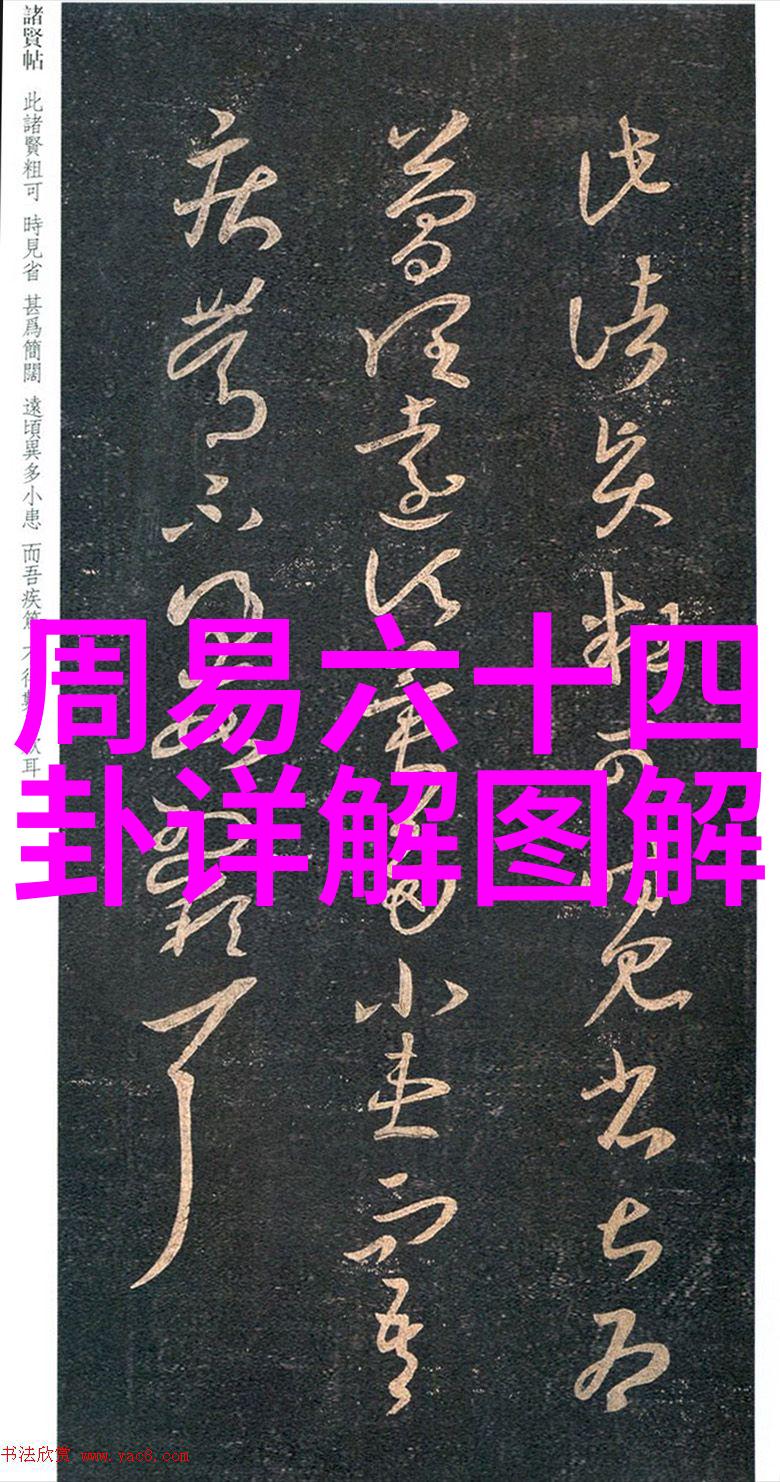清水里的刀子策划人解密西海固若有倾听肯与倾诉
备受瞩目的电影《清水里的刀子》将于4月4日清洁上映。影片讲述的是西海固那片土地上老人和牛的故事。对于西部地区的回族观众,西海固或许已太过熟悉,但东部地区以及兄弟民族的观众,很多人还并不能明晓西海固的含义。为此,应观众需求,本刊特发专稿,为理解西海固提供一个新锐的触角。 西海固究竟是什么?十数年来,我苦索着答案。 几度放浪于黄土深壑,在密如历史的群山褶皱中穿行,我在叩问,难道西海固就是人皆言之的苦难的代名词么?仰望无遮无拦的天空,天空寂寥;环顾无边无际的群山,群山无言。我隐隐明白,西海固不同意那肤浅的回答!可是对闯入者,它宁愿板着一副冷峻而决绝的表情,以近乎顽抗的缄默形象,凝固成一个任人误解的谜语。 在知情者的眼中,西海固太过有名,那三个可以分离的汉字,每一个都竖起尖尖的毛羽,随时准备冲天一怒地高高飞起。在不知情者看来,它又太过陌生,陌生到像这里的雨水一样,可以被随意地忽略不计。 有人说,西海固的名字本身携带着一丝神秘色彩。其实,作为一个地理共同体,西海固的概念并没有那么深奥难解。1953年,国家以六盘山以北的西吉、海原、固原三县为主,成立了西海固回族自治州。后来,自治州的建制随着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成立而被取消,但人们好像舍不得忘记这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即便在行政区划上已成为历史的旧物,而在人们的情感深壑中,西海固还是更多地作为一种文化标符,被牢牢地凿刻了下来。 今日的西海固,实则已经成了宁夏南部山区的统称。它大体上包括:宁夏固原市的原州区、西吉县、泾源县、彭阳县、隆德县,中卫市的海原县;也有人认为,从相似的地貌和人文环境上考量,吴忠市的同心县、盐池县也可并入其中。 西海固越来越大了,大到塬峁苍苍,流沙鳞鳞,何处有苍凉便与它有关;西海固也越来越小了,小到变成了“针尖上的蜂蜜”,深埋在谷底的一抔乡愁。 一 西海固,是一片海。 只是用石舒清的话说,“这是世界上最缺水的海”,“有的只是这样只生绝望不生草木的光秃秃的群山,有的只是这样一片旱海”。 旱海,作为对这一带惯用的一种描述,古已有之。 黄河流到这里,开玩笑似的拐了一个弯,留下一座高高大大的六盘山,把雨水死死地拦在了山外。这里属温带性半干旱—干旱气候,全年无霜期达100天,年降水量只有300毫米,蒸发量却是降水量的10倍,是地球上有名的水源奇缺之地。1972年,粮食开发署把这里确定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 所谓滴水如油,大概只能在这里找到应验。 在许多的描述中,仅有的水,是低洼地带汇集的雨水。石头井中储存的已经是“好水”,冬天上山搬来积雪块,融化了够喝一年。“娶妻说媳妇,先要显示水窖存量;有几窖水,就是有几分财力的证明。”更多人则是在随意挖的土坑或者小水沟里提取咸水。但就是这样的“坏水”,仍然是金贵的。 家家惜水如金,洗碗也只是用抹布直接擦拭干净。天阴欲雨时,人们会穿上薄一点的衣服到地里,一边干活一边等雨。雨后回家,赶紧脱去衣服,把身体擦干,就算洗过澡了。当地人把这叫做“趁雨”。 无水的极处,便是苦甲天下。所辖七八县皆是国贫县。尽管在人口和土地面积上占宁夏三分之一,但国民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均不足十分之一。1982年,西海固与甘肃的河西、定西被列为全国首个区域性扶贫开发实验地,因都有一个“西”字,统称为“三西”地区。国家每年拿出2亿元,计划用十年时间使其脱贫。但时至今日,除了河西迈入小康行列外,余下“两西”地区仍是远近闻名的贫困之冠。 自然灾害格外眷顾于此。最著名者当属1920年的海原大地震。8.5级,裂度达12度,地广人稀的西海固有二十多万人消失于一瞬,压死生畜,倒塌房屋、窑洞更不计其数…… 然而,就是在这“不适合人类居住”的沟沟峁峁,却生活着一百多万回族乡亲。他们和毗邻而居的兄弟民族一道,匍匐在黄土高原的塬、峁、梁、壕之间,厮守着枯干无望的运命。有人觉得讶异:这个民族的祖先沿陆海丝绸之路而来,基因中本都长于经商、头脑灵活,多选在山清水秀、水草丰茂之地,或是那繁华辐辏的城关中心落脚,怎么偏偏这一群流落在如此苦困至极的山沟里? 只有走进西海固尘封二百余年的精神秘史才会知道,原来这些回回人的先民并不是生而居此的——他们多祖居富庶的秦川,也曾衣食无忧、铜山金穴,只是不公正的历史把他们从家园驱逐出来,便一步踏进了雄关漫道的迁徙史。 他们是流民的后代,难民的后代,幸存者的后代。 靠什么生存下来呢? 唯有凭靠冥冥中的指望,精神之树上最后一片信仰的树叶。 二 俱久矣,泰山若厉!群山之巅的秘密无人公布,更无人知悉。 直到1984年冬月,一个作家在一场带有神示气息的大雪中潜入这“无鱼的旱海”,自此泥足于热浪田间,问道于万户农夫,历经六年写出震动文坛的一部巨著,更多世外之人方听到了“西海固”这个干涩、炽烈、坚硬的名字。 “学生们个个发愤读书,为的是逃离家乡”,“女人们嫁不出去,她们穷得往往没见过邻村,没有一身衣裤”。书中写道,1960年前后的“自然灾害”期间,沙沟流传下这样的故事:一个孩子进山挖苦苦菜,连挖开地皮的力气也没有了,死在能救命的野菜旁。同伴吓得跑回村,告诉那孩子的母亲。她刚刚弄来一碗糊糊汤,正打算给儿子喝,一听说儿子的死讯,竟“猛地抓起碗,只顾自己急急地喝起来”! “那时的沙沟——狼和狐狸在一家家屋里串窜。有一个女人病在炕上,狼进了屋。而人们却以为是狗,睬也不睬。” 北京电影学院的课堂上,最有思想的老师会告诉学生,“饥饿”的表述怎样才算是到位?只消去读读张承志写的西海固。 有人读了,就一定要跑去,亲眼看一看那是不是真的。 什么是西海固?多少次,我追索无眠。 深远的夜空,浩大如谶。 在张承志的另作《离别西海固》中,有这样的名句: 西海固,若不是因为我,有谁知道你千山万壑的旱渴荒凉,有谁知道你刚烈苦难的内里?西海固,若不是因为你,我怎么可能完成蜕变,我怎么可能冲决寄生的学术和虚伪的文章;若不是因为你这约束之地,我怎么可能终于找到了这一滴水般渺小而纯真的意义? 大概是外来者最极致的抒情吧。 它使我们知道:在“千山万壑的旱渴荒凉”之间,更重要的是那“刚烈苦难的内里”。 西海固的本土表达,究竟来得过于迟滞了一些。这里的人们不擅于言说,更不愿意言说。但机密还是势不可挡地被打开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作家密集地出世了,他们用小说、用诗、用散文,敞开被压抑太久的心情。文学圈子里流传着一句话:“在西海固,不长庄稼,只长作家。”也有人不以为然:什么叫不长庄稼?洋芋不是庄稼吗?到处都是洋芋啊。就把这话改成:“西海固只长洋芋和作家”。这么一改,听起来倒愈有些苦涩。 作家真的可以与洋芋一起,旺盛地生长出来吗?海原出了石舒清,同心出了李进祥,西吉出了马金莲,还有左侧统、古原、单永珍、马占祥、泾河、了一容等等,不胜枚举……一言蔽之,当前回族最活跃的小说家、诗人,近半云集于斯。至于每年每月从各个县乡冒出的文学青年,俯拾皆是。西吉,便这样成了全国挂牌认定的第一个“文学之乡”。西海固的文人们,忍受着无人喝彩的寂寞,让方块字在多难的母土上开枝散叶。 有人说,他们是一群黄土地上的文化囚徒。 也是始自少年时代,东北边城的我通过石舒清的文字认识着遥远的西海固。较之于令人窒息的历史,他更在意一种日常化的“在场”讲述。于是,我看到了院墙间、老屋里,那些喂鸡的盲童,跑着揉面的女孩,待嫁的新娘,织毛衣的老人,生死相伴的夫妻,站“者那则”的人群……他们从容、温暖,静如止水。 《清水里的刀子》并不一定是石舒清最好的小说。但至少目前,它最有名。它在文学界的有名,并不是由于苦难的轻重,而是由于对死亡的理解。如果你想读懂西海固的眼神,真正的内行会这样指点:从死亡开始吧;即使对于幅员辽阔的国度来说,谈论死亡常常是一种禁忌。 一个失去老伴的老人,一头即将被宰的老牛。他们在临界死亡的道路上,相互珍惜着,经历永恒的时间。 小说是简单的,但它提出的命题无比重要:死亡与高贵。即使死亡,也要带着清洁的内里,高贵地离去。这并不是石舒清一人的发现。在张承志的《最净的水》中,在李进祥的《换水》中,马金莲的《长河》中,“水”所带来的清洁感对于一个民族的重要,几乎是一个常识。这种对清洁精神的迫求,或许并未遍布于文学界,而在西海固的叙事里,恰恰最为集中。 这是《清水里的刀子》以六千余字成为经典的秘密。 这是西海固的人们,更为内在的本质。 三 2007年的夏天,烈日如炙。因拍摄有关西海固的三部电影短片(其中包括《清水里的刀子》短片版),我和大学同学王学博在尚未毕业的时刻,与一群有着共同梦想的伙伴相约来到了沙沟,西海固的腹地深处。 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西海固。 群山,还是群山!黄土地袒露的胸肌上,网布着深刻的伤痕,每一棵苜蓿草和矮玉米的眼神里,都写满对生长的奢望。有那么一瞬间,会觉得那漫山遍野的单调,在蓝天的比衬下有一种油画般的美丽,可是你会突然发现,身旁的老乡眼中没有你的赞叹和兴奋,他们说,有啥美的,能长庄稼的地方才美呢。 于是,那迷人的风景又忽然叫人想哭了。 它真实,赤裸,记录着一种叫做坚韧的人道,也告诉来到这里的过客,背负苦难的迁徙史是一种很难被扮成“苦难美学”的历史。一切都是真的,以往只能在文学中遥望的情境,一幕幕地兑现了。张承志没有说谎,石舒清也没有说谎。 但我必须坦言,西海固绝非你们所想的那样苍凉到底。这里其实是有绿色的,它们挣扎在黄土的缝隙里,覆盖在寂寥的山坡边,涂染在清真寺的塔尖上。那是一片像水一样叫人沉醉的绿! 也会有那种罕见的大雨,这是先前谁也未曾预料的。像是苦苦憋了几个世纪,一下子要下饱、喝透,雨点如豆,黄土小径很快流成了水汤,溅起高高的泥团。连片连片的向日葵在暴戾中把头艰难地扬起,打在花杆上的雨声劈啪作响。途中,路经海原一个叫李俊的小镇,在一户农家避着雨。头戴方帽的女主人端出满满两大盘西瓜,又送上馍馍。难道要一起吃么?半晌才知,就是这个吃法,而这两样看似不搭界的食物一起在口腔中搅拌,竟是别种美味。 每一天,从一碗沉甸甸的臊子面开始,走在一条条乡间土巷。每一晚,在占了半间屋子、散发着呛人的牛粪清香的大炕上入睡,夜幕里长风呼啸,门窗作响,起夜时可以看到硕大如斗的星星。闭上眼,是那土的带着凹洞的泥墙,是那屋脊上停栖的泥塑和平鸽,是那挑水娃、放羊娃变声期的笑喊,是那被狗咬的男孩身上的斑驳血迹,是那开满土炕的绣着彩色鲜花的鞋垫,是碎媳妇扫着院子时忽然吼出的几句叫人心疼的山花儿…… 西海固,在每一个昼夜,以永恒不变的姿势向我们打开。 印象很深的是,每家每户的宅院间隔很远,每过一户,无须担心斜视与诘问,那主人必会掀起碎布拼接的门帘,邀你进屋去坐,没等说上些什么,案板上剁菜的声音已经悄悄响起,不吃不行了。如果急得连口茶也没有喝上就走了,主人真会生你的气。他认真地吼着,这是我们的礼性! 全无客套,全出本然。即便贫穷刻骨,也要把尊严高高扛起。无以复加的自尊,渐渐变成了加倍待客的方式。只有亲身相遇过这山野间的重重礼性,才会忘记遍体鳞伤的穷困,相反却猛地感到:分明最富裕的人类就在近前,最浩大的水流正在淹没干旱。 如果不是这样走进了你,西海固,你那缄默千年的密语还将封藏到何时?此后我长途流徙,此后我辗转流连。明白了什么叫九彩坪,懂得了什么是西吉滩。 从紧紧抱住书本,到双脚沾满泥泞;从茫荡的群山大地,到一张张诚恳具体的面庞;从记者式的提问,到方言俚语,抵足而眠…… ——这需要时光付出多么足够的诚意! 我作证,西海固没有拒绝过任何一次或真或假的访问;但我彻知,敏感的西海固,它暗暗检阅着一切。 四 早已有人预感到危机。 他们发现:源源不断的支教大军、慈善爱好者、心存浪漫而决意苦旅的背包客,前赴后继地涌入了西海固。更多的摄影家们,则端着长枪短炮,“在黄昏的清真寺外守候,在劳作的田间跟踪,或者对着一口枯井狂拍”。 诸如被誉为“西海固影像代言人”的王征那样,无意识的、自然生长的、不刻意展览贫穷的摄影创作,毕竟太少了。 在一篇名为《西海固:在影像里沉沦》的文章里,出身土著的文化人海杰尖锐发声:“西海固正在变成,变成福建霞浦,变成元阳梯田,甚至变成岜沙,成为新一轮的影像开采地。”甚至他不无夸张地假想,“若干年后的一天,在部分被视觉传播强化的西海固地区,会涌现出不少木屋酒吧、青年旅馆以及孤单出行的以寻找游伴贴条为主要表达方式的剩男剩女。” 无疑,暴露在广角之下衣不蔽体的西海固,正迎接着一轮接一轮的围观。 表现西海固,在一部分陌生人看来,是前所未闻的创举,是带着人文温度的抚慰;而在另一部分人看来,却无异于文明的殖民与掠夺。 我们都曾是闯入者。 我们当年的冒访,尽管满怀善意,却是否无意之间也曾坠入哪怕些许的窠臼?我们的影像表达对于西海固,意味着帮助还是伤害?我久久沉思着这样的疑问。 分寸尽处,乃是人心的天平。 有一天,当王学博决定把学生时代的习作废掉,重新把《清水里的刀子》拍成一部具有国际影响的长片时,我曾严峻地提示他,触碰西海固可能遭遇的困境与争议。 我是真想做,我该怎么办?他陷入了焦灼。 把自己化成西海固的一粒沙尘吧,当你真正地想去倾听时,它一定会对你倾诉。我是否说了类似的话,记不清了,只记得转眼间,王学博不见了,他离开租住的北京胡同,独自一人重返西海固,开始了为期十个月的体验。 体验生活,好像是第五代导演才会有的提法。但王学博真的去了。他的决绝超越了我对他的理解与想象,也超越了我所能企及的边界。 再次见他,已是通身黑瘦,带着一口奇怪的音调,浑身散发着浓郁的牛粪味,洗了多遍仍未消散。在无数的辗转、等待、忍耐、爆发、哭泣、喜悦中,机会终于到了,遂再次奔赴。至影片定剪之日,与我们初入西海固之时算起,时光已刚好走过十年。 韦应物有诗云: 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 西海固是否需要表达;如若需要,如何表达?作为闯入者的王学博们尽管付出了身心足够充分的诚意,用无意识的、自然生长的、不刻意展览贫困的镜头记录了西海固,但这样混沌驳杂的命题,追索似只是刚刚开始。 西海固,更像它的原始古称“萧关”那样,把自己围成了一座孤绝千里的城池。城外的人对城里喊:不要再写了,写得那样苦,靠兜售苦难博得关注与同情;我们的民族并不都是这样的!城里的人们感到委屈,生活原本如此,难道不允许真实地书写他们所经历的一切?苦峻的旱海并不是言说的要义,他们要言说的,是旱海里最鲜活最具有生机的一条条鱼。 而更多时候,城里的人们也会对城外:采掘完苦难变成书和影像就走了,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带来了怎样的好处?时间久了,他们愈发地敏感和易怒起来,不喜欢有人谈论他们的家乡:夸奖吧,觉得你虚伪;批评吧,难以赞同;最要命的则是怜悯抑或同情,那一定是令人生厌的忌讳。没有人有资格怜悯西海固!西海固不相信眼泪! 岂止是他者;也许存在这样一种特型的西海固人:当他踏上了远离母土的长旅,改换了口音,跻身于北上广的主流社会时,连他自己也很可能拒绝谈论西海固,甚至把与生俱来的身份密码本能地忘却;倘若有知情者认出了他,提醒了他,与他亲切地拉手叙旧,他反而轻蔑地一瞥,转过脸去。他未必不爱他的故乡,只是他觉得对于西海固,最好的方式便是博物馆的方式:把窗帘拉上,在避光的玻璃柜中收藏起来,你可以偶尔地看一看,但永远没有资格打开。 这或许显得狭隘。 可是想想看,有哪一个贫穷的孩子愿意有人每天谈论他的贫穷?对于特殊的西海固,任何一种特殊的心态都应该得到理解。 或许让那个孩子安静地独坐角落,不要去看他,也不要指点、关爱,直到他有尊严地慢慢长大,强健,富足,告别那使人难堪的过往。这是一种爱。 然而,他的童年却一定是孤寂寡欢的。如果换一种活法,每个小伙伴都可以大声呼喊他的绰号,穷孩子、富孩子,一起在泥地里打滚,甚至也有不懂事的小孩指着他的补丁嘲笑几句——起初他当然是愤怒的、自卑的,可是听得多了,他又觉得这十分无聊:穷能够代表什么?真正的贫穷,是知识的贫穷、精神的贫穷、道德的贫穷。想开了,也就不用再纠结,没准再听到谁戳他的痛处,他却哈哈大笑起来。他对尊严的认识更加主动,也更加勇敢,他不惧怕穿着补丁拍照,却在心里暗暗较劲:明日再论英雄……这样的孩子,往往心志强健,经得起挫败,也不会因一时荣华而忘却来路。 愿意做哪一种孩子?选择权只能交给孩子自己。 唯须倡言:为西海固表达的资格,并不一定只属于那片土地自己;他者的言说,一样是必要而珍贵的。资格的选定与自己人还是局外人无关,与是否也穿着同样的补丁,受过同样的苦和难无关,前提只在于:那颗跳荡的心是否端庄,洁净,真挚,是否懂得西海固的心。 五 今天再来谈论西海固,若仍然只把干旱、贫困、坚韧作为关键词,不仅是缺乏知识的,也可能是缺乏道义的。 是年春,当我再次站在当年曾经环顾群山的沟梁上寻望,那曾经光秃秃的荒山上竟然开满了红艳艳的桃花。乡亲说,退耕还林了。 缺水的情况固然仍在,但多数已通上了自来水。 女娃娃都上了学,太多走进高等学府,又读了硕士、博士……不再可能只上到三年级,就被赶回家里,十五六岁就早早嫁人。 广袤的宁南山区,移民搬迁工程正在进行。一个个窑洞废弃了,黄泥小屋成为留在文学史里的意象,几百年世居的贫瘠山村,在老人深情的回望中成为标本。 西海固,源于迁徙,而奔向新的迁徙。它从未有过如此鲜活的运动感,从未灌溉过如此充盈的时代讯息,故而相应地,它也慢慢适应了世界的观察和提问。 如果历史注定重现,今天的西海固就如同它曾经骄傲的过往:丝绸之路从身上穿过,各国商旅在这里贸易。凉秋八月萧关道,走过了王昭君、蔡文姬,走过了王维、岑参,弥漫过铁蹄厮杀的吼喊,还有无数牵动情肠的悲歌咏叹。 西海固的称呼不需要消亡。我期待有一天,它可以足够强大地包容一切表达——自我的和他者的,善意的和恶意的,爱护的和伤害的——都能微微含笑,羽扇纶巾,绝不必敏感地虎视眈眈,随时准备顶起自卫的犄角。 西海固,能够习以为常地面对一切对准它的镜头,不论长枪短炮、横拍竖拍,它都不需要紧张地回避,更不需要迎合地表演。日常如旧,该是什么样子还是什么样子,还是拔高都与它无关:它永远是那个安静从容的最好的自己。 西海固的大门永远向着善意的访客洞开,永远像从前的日子一样把他们热情满满地让进屋,茶沏上,臊子面下上。倘真有人愿意倾听,它便欣然开口倾诉,平凡如家常絮语,神色亦宠辱不惊。 到何时,如果不把自己当成西海固的西海固,西海固就成了人类的西海固、世界的西海固、多种色彩的西海固。而这本来就是它最美的模样。(作者石彦伟)